为裂痕中的青春铺上缓冲垫
▌仇士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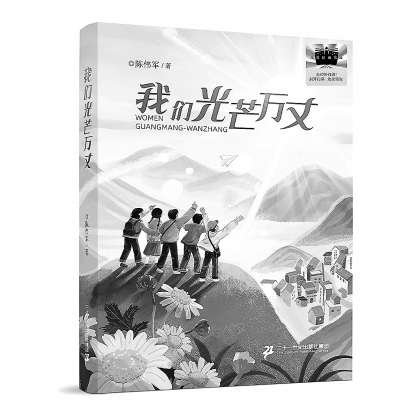
《我们光芒万丈》 陈伟军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有人说,最稳定的家庭关系,是三角形。父母与子女各占一角,家岿然屹立。但若是父母离异了呢?三角形就开始变形。《我们光芒万丈》探讨的就是离异家庭里,青少年作为被动承受的一方,在这场成长不得不经历的风浪里的困惑、挣扎与渴望。
作者陈伟军施展了巧妙的魔法,他在千人千面的故事中,翻动着家家都有的难念的经,一些押着相同韵脚的叹息便清晰、响亮了起来。侯小阳、毛一蔓、彭奇、江洋……乍一看,一个班里,竟有这么多离异家庭的子女?事实是,我国的离婚率的确呈现增长的趋势,因此带来了各式各样的家庭问题。
心理学上,常用“危机—弹性”模型阐释父母离婚对子女的影响。危机有很多,情绪、认知、行为乃至人格发展都会受到冲击。尤其是父母任意一方的缺席,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,都会让子女的依恋如霜打的茄子。失望攒多了,就发酵成了恐慌担忧,风雨飘摇的归属感演变成被遗弃的妄想。
弹性则像缓冲垫,它提供的韧性支撑,能极大地化解危机的冲击力。
首当其冲的缓冲垫,是自身的抗逆性。有学者将它分为三种层次:生存层次、防御层次、健康层次。前两者通过有暴力倾向的行为或压抑封闭实现自我保护。书中,侯小阳都11岁了,仍固执地相信那些6岁的孩子才会相信的童话——他是蚂蚁王国的王。因为这个故事是父亲告诉他的。父亲还说,他离开这个家,是去执行王国的绝密任务了。某种意义上,侯小阳的天真幼稚何尝不是对父爱日复一日地翘首以盼?仿佛只要他还相信着这个故事,父亲就有重回家庭的一天,而他也始终不会长大,会停留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中。
也因此,他想破坏母亲和毛叔叔的重组,为父亲的归来扫清障碍。侯小阳并不知道如何保护心中的那份柔软,只能长出刺,以对抗外界的刺激。那些不能化解的悲伤与不愿承担的重量都铸进攻击性里,却又会为不懂事和惹事闯祸的标签添上新的“罪证”。久而久之,他们身上就扩散开不合群的磁场,并且在社会所期望的“正轨”上步履蹒跚。
健康层次则显出亲社会的倾向,有着千磨万击还坚韧的成长性。不再逃避、勇敢直面,是化解心理危机的对症之药。被雨拦住、止步不前的人,眼前只会有雷电、风雨和泥泞,但穿越过去,会看见豁然开朗的万里晴空。很多时候,只有当友善、乐群、自信等词语从心头拔地而起,才能用它们的叶子汲取到更多的阳光雨露,去光合作用,去含香吐翠。
第二张缓冲垫是父母织成的。侯小阳很幸运,父亲时不时地会来看望他,并与母亲、毛叔叔商量对他的教育。这样的三角形,纵使父母之间不再是实线,整体依旧是牢固的等边三角形。更何况,毛叔叔诚心诚意地对待他,和谐的重组家庭关系如《家有儿女》般,让他身下的缓冲垫又多了一层,保证了青春期的叛逆平稳落地,摔不出锋利的碴口。
彭奇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父母离婚之后再没有交集,一年才看他两回,他只能和爷爷相依为命。当父母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,家庭被拉成又长又扁的钝角三角形,它就再没有等边时的稳定性,一点外力便能把它压得变形。
最后一张缓冲垫来源于社会环境。比如学校、老师。书中,班主任的包容与鼓励让侯小阳发现,他在别人的眼中并非彻头彻尾的麻烦男孩,他也有被人赞叹的闪光点。在渴望爱与尊严这个本能最蓬勃茁壮的年纪,老师就像一个温润的光源,让黑夜有了萤火、有了月华甚至破晓的曙光。事实上,陷入茫然的青少年,往往只缺少一个安全而坚定的立脚点,就像植物,不管抽枝拔茎多么迅速,都要在稳稳地扎根后才能进行。
朋辈的支持、群体对个体的拥抱与感召亦是青少年解开心结、改变自己的强劲动力,毕竟读书期间,他们最多的时间是生活在朋辈中。书中,伙伴们放飞心情,从悲伤转为快乐的节点,就在于敞开心扉后,在信任与关爱的氛围下,分享了自己寻找阳光的方法。于是,个人的一束光汇成了群体的一片光,在这光里,那些伤痕累累的心照亮了自己,也照亮了别人,焕然一新、光滑如初。
人们常说,不幸的童年往往要用一生去治愈,但如果有足够的弹性,家庭变故的危机产生的影响就是有限的,就像把染色剂丢入河流中,在一定距离外,水会恢复清澈的本色。此外,祸兮福之所倚,有时候,父母离婚的危机也是一种机遇。书中,父母长期处于冷战和热战的交替,猛烈的摔门声不啻炸弹……这些在江洋的心中留下难以修复的创伤——在子女那儿,家庭施加的痛苦是双倍的。而当父母用离婚终止了拉锯战,对江洋来说,短痛之后,长痛也画上了句号,风平了,浪静了。
书中,我还看见了优势视角理论的影子。它着眼于个人潜能的开发,认为即使是最可怜的,被社会抛弃的人都有内在转变的可能。欺负过彭奇的混混,在侯小阳急需雨伞的时候,主动把伞递了过去。可见,善与恶从不是非黑即白,就像江洋会当告密者把毛一蔓偷带手机进校园的事捅出去一样,善恶会在彼此的身体里共存。而教育的意义就在于让善的树冠荫蔽更多的土地,用根系束缚恶的肆虐。对恶的控制与感化,也必定会成为自身抗逆性的一部分。
合上书,印象尤深的是,陈伟军很擅长用物象作为线索,比如纸飞机、树叶和乐高积木等,去串起故事情节,并将这些物象置于大环境中展开描写,去首尾呼应,或作为紧密的情节外荡开的一笔,如一个安静的、拉长的电影镜头。既隐喻着人物的情感变化,又让那份属于青少年的悲喜在落日中、在大雨里、在小径上,停留得更长久,抒发得更委婉。
故事的最后,侯小阳收到了父亲寄来的蚂蚁国王的设计初稿。不被亲友理解,不惜远渡重洋追寻动漫理想的父亲,也迎来了他的曙光——策划的创意卖出了版权,即将落地成一部响当当的动漫电影。那是关于蚂蚁王国的故事,更是他与儿子最初的、最动人的童话约定。陈伟军并没有写明蚂蚁国王的具体形象,而把它留作一个悬念。或许,是因为他不想去束缚读者的想象力,也或许,是因为每一个相信蚂蚁王国故事的人,都组成了蚂蚁国王的形象。